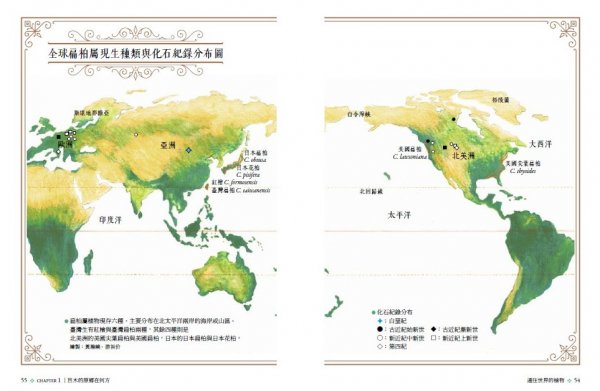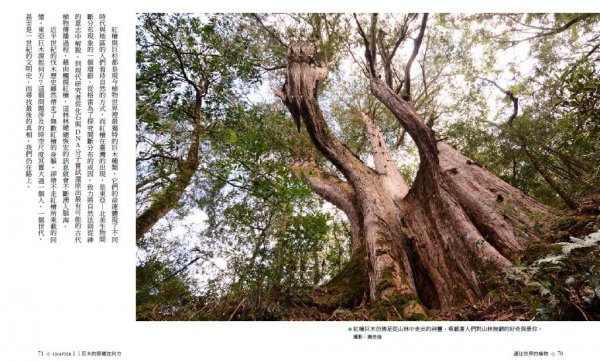2020-08-09 09:11 聯合新聞網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受訪者游旨价,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博士,著有《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一書。(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受訪者/游旨价
圖/游旨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臺灣的高山它哪裡的高山都不是,它就只是它自己。在冰河的往復之中,迎接來自他方的旅者,創生自己的後代,在島嶼上留下了獨一無二的歷史。 ──游旨价,《通往世界的植物:臺灣高山植物的時空旅史》 |
您為何會投入植物學/生物地理學的研究?
也許一切可以追溯到15年前的森林系,那時大一的我選修了植物地理學這堂課。我好奇為什麼「植物」和「地理」兩個字結合起來,竟然可以變成一門大學課表上的「專業」課程?
課程名稱裡的「地理」一詞,並沒有跟著學期的結束而離去。後來我參加了登山社,才第一次體悟到臺灣這座島並不小,如果把層層疊疊的山地也算入的話,臺灣其實很深、很寬闊。大學畢業時,植物地理學中的另外一個字──「植物」也找上了我。我從指導教授手中接下了小檗的分類學工作。當時,小檗多變的形態一直令我十分困擾,煩躁之餘,我開始留意起植物的分布地,從中注意到「地理」尺度的變化。
我開始理解植物雖然不是動物,但不代表它們是不「動」之物,甚至還具有傑出的旅行能力,導致它們的分布樣式竟是如此饒富趣味。比起分類植物的形態,我似乎更著迷於歸類植物的分布格局。而想要連結分布於各地的植物,便需要知道地球與自然的歷史。

玉山之巔的玉山小檗(圖/伊東拓朗攝,游旨价提供)
就您的學科來看,您會怎麼理解移動這件事情?而19、20世紀的異國旅人來到東亞,甚至是到臺灣進行採集,您認為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
移動必有方向,也必留下痕跡。當代植物地理學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在於還原植物移動的歷史,所以他們的移動其實是在四處「蒐集痕跡」。然而,對19、20世紀的異國旅人來說,他們許多人當時仍處在四處「發現痕跡」的階段,他們來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對臺灣島的未知進行科學探索。
解讀痕跡,往往比發現痕跡還要來的困難費勁,我們雖然因為時代因素錯過了「發現痕跡」的階段,但此刻解讀痕跡的工作仍在路上,值得所有對臺灣植物有興趣的人們投入。
19世紀來到臺灣的歐洲植物學家、博物學者,與再之後日治時期來臺踏查的日本博物學者們,在背景與企圖上,有什麼不同之處?
日本做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在殖民地臺灣島的物種採集成為彰顯國力的必要行動。然而臺灣島的自然科學史並非始於日本,19世紀中葉的清領時期,英國人早已藉由中國開放通商口岸的契機,首先來到臺灣島從事自然科學考察,彼時島上特有物種逐一被披露,臺灣也以「Formosa」之名開始在歐美學界傳揚開來。
儘管如此,由於清廷勢力無法進入高山的「生番」地界,加上採集活動多是零星的個人行為,而非國家支援的計劃,19世紀的西方人終究錯過了臺灣陸域生物多樣性最精彩的高山地區,僅能有限度地探究臺灣的自然風貌。但日本政府經過19世紀末明治維新科學研究的實踐,在臺的植物考察不僅是有財政挹注的官方活動,也身負在殖民地貫徹帝國主義的期待。博物學者身處這樣的大環境裡,除了有與其他來臺歐美學者競爭的壓力,也有統治目的的考量。

臺灣杉,收錄於森丑之助與中井宗三著《臺灣山岳景觀解說》新高堂書店1913年發發行。(館藏號2002.007.0007.0018)(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雖然對自己的工作目的有所覺悟,但在科研活動中與臺灣島土地、在地原住民之間培養出深厚友誼的博物學者(如鹿野忠雄、森丑之助),多少還是有對殖民主義產生反思。而此般對臺灣島風土民情的人文關懷,相較於其他早期來臺工作的歐洲學者,也許也能算是在臺日本博物學者的一項獨特之處吧。
那麼,19、20世紀來到臺灣的日本學者,是在怎樣的背景知識下看待、理解臺灣的高山植物?如何將他們的發現擺放回殖民母國的知識網絡中?
日本領臺初期,日本學者在臺灣高山的植物調查活動,其實與臺灣總督府的理蕃、開發物產政策有著密切關聯。彼時,因為總督府亟欲瞭解臺灣高山地帶有哪些自然資源值得開發,在負責調查臺灣產業相關資源的殖產局下,設立了「有用植物調查」的臨時單位,聘請學者主持調查計畫、鑑定和分類植物標本。
在那個年代,日本學者的學術研究若在國際有所成就,經常與國策規劃脫不了關係,與日治後期的氛圍不大相同。後者(譬如鹿野忠雄)的成就大抵源於自發性學術活動的結果,與政策較無直接關聯。不過,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哪個時期的學者,他們在臺灣島的科學成就,還是都被作為彰顯國力、樹立權威的證明。也因此,一旦殖民帝國/母國認為臺灣的「高山植物」以及「高山植物研究」都是有用之物,日本學者在臺灣高山的探查就得以持續,間接地造就「臺灣植物命名大時代」的來臨。

鹿野忠雄著《山和雲與番人:臺灣高山紀行》,被譽為日治時期「日本高山文學三大名著」之一,為臺灣高山文學的經典。鹿野忠雄是博物學家、民族考古學者,此書是其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就讀時至臺灣進行登山勘察的紀行文章。(館藏號2011.012.0299)(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最後,在您的著作《通往世界的植物》一書中,提到19、20世紀的博物學家時常在探險異地高山時被勾起鄉愁,有沒有什麼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
上個世紀上半葉,靠著在高山踏查的實踐,日本籍的博物學者成為了最瞭解臺灣高山植物的一群人。這份瞭解不只反映在知識上,也在情感上形塑出無形的羈絆。臺灣島是他們許多人在海外工作的第一處地點,而臺灣的高山植物意外地引發在臺日本學者獨特的心情波動,譬如鄉愁。然而與其說有特定的溫帶植物引發鄉愁,不如說被高山整體植物相的風景觸動心弦更為貼切。這種幽微的心境轉換,也許可以從鹿野忠雄攀登中央山脈達芬尖山的紀錄裡窺得一二,他寫道:
「寬闊的草生地,到處都是藍色的龍膽花和粉色的石竹花,盛開的高山野花向藍天微笑著,⋯⋯陣陣松籟傳來,引人遐思。⋯⋯這樣的景色讓我想到(日本)內地夏天的避暑勝地,沒有人工雕琢,只有無為自然、安逸悠閒,甚至引起了我的鄉愁。瞬間,我想到,我為什麼要辛辛苦苦老遠跑到這個地方呢?」

中央山脈的春色,收錄於森丑之助與中井宗三著《臺灣山岳景觀解說》新高堂書店1913年發發行。(館藏號2002.007.0007.0015)(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不論哪個時代,科研工作的氛圍都是漫長的孤獨,鄉愁是他們通往遠行前人生的橋梁,令他們憶起自己啟程的決心,為自己在異地工作的心情找到寄託。這也許也是為什麼當年日本博物學者除了留下諸多科學論文,也寫出了這麼多的文學作品的原因吧。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6期「在福爾摩沙旅行」。
資料來源:udn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