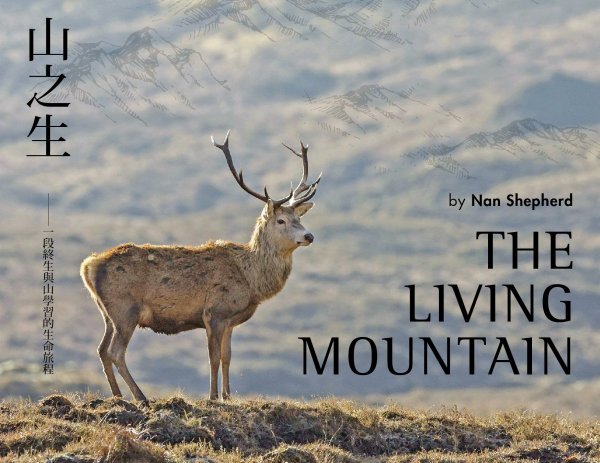※本文摘錄「山之生」
第七章 生命:植物 Life:The Plants
到此之前,我寫的都是沒有生命的物質,比如石頭與水,霜和陽光,好像這裡不是個充滿生機的世界。其實我是想先描寫孕育萬物的自然力量,再一步步靠近山間的生命。大山畢竟是一個無法切割的整體,山裡的岩石、土壤、水和空氣相較有靈魂、能呼吸的活生物都是不可或缺。一切不同元素都歸屬於活生生的山。崩裂破碎的山岩、滋養萬物的雨水、令萬物復甦的太陽、種子、根莖與鳥獸,皆為一物;鷹和婆婆納(alpineveronica)也是大山的一部分。虎耳草之於大山,猶如眼瞼之於眼睛;假如沒了大山,虎耳草這種「碎石者﹂就難以生存,其中最可愛的星虎耳草(Stellaris)和黃山虎耳草(Aizoides)也難覓其蹤。星虎耳草單朵的小花似星星般鋪滿高處窪地的溪流,黃山虎耳草則像溫軟的陽光,在河流下游叢生。

高原上隨時有可怖的暴風,生命能夠倖存已是奇跡。就海拔來看,這裡不算太高,植被可以生長在遠超過四千英尺的地方。難的是這裡沒有庇護所,唯一勉強稱得上庇護所的只有沿著寬闊斜坡流向峭壁的水流。能夠生長的一切都暴露在浩瀚無邊的空氣中,大風從冰島、挪威、美國、庇里牛斯山脈呼嘯而來。高原的地表起伏波動,既沒有石塊、也沒有深谷能為植物提供安靜的生長環境。不過偶爾和我結伴同行的植物學家告訴過我,那裡有超過二十種植物,假如算上苔蘚、地衣和藻類每一物種的不同形態,數字還會更大。他為我列了清單,讓我可以一一辨認。生命,似乎不理睬惡劣環境的警告。
生命的韌性不僅體現在山頂,也能從較低處那些石楠被燒焦的山肩看出一二。石楠承受烈火、嚴霜、狂風和其他險惡氣候的能力眾所周知,而早在其焦枝下方的根部顯出復甦的生命跡象或隱藏在土裡的種子重新發芽之前,百脈根、直立委陵菜、藍莓、小小的金雀花還有斗蓬草就已經突破土壤,伸出蓬勃的嫩芽。這些山花的纖弱難以用語言傳達,它們的根莖纖細,花朵柔弱,但只要向其靈魂深探,就會發現永恆耐力的根源。或蜷伏成團,或纖長如絲,它們就像一塊塊死木和一條條筋脈,在土壤下保存了植物生存的必備能量。即便在地表以上的所有生長都已停滯—無論是遭火燒、霜凍還是漸漸枯萎—這裡依然生機勃勃。不管任何時候、任何季節,山都因它們的存在而生機勃發。就算根被摧毀,泥土裡仍然保有活著的種子,準備好重新開始生命的迴圈。世上再沒有比這裡更能夠證明生命不可戰勝的力量的地方。一切都在設置重重阻礙,生命卻毫不理會。
高原上的植被形體矮小,因為緊貼地面生長,連風也難以抓到任何鬆動的末梢。它們或在地表上蔓延,或在地面下爬行,或緊緊抓牢與其外在生長形態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根莖。我曾說過它們毫無庇護,但對任何一朵花來說,群體本身就是庇護所。高山花朵裡最令人驚歎的當屬蠅子草,一簇簇明亮的粉色小花開在六月及七月初,散落在最貧瘠、石頭最多的地方;生長習慣和紫羅蘭類似,密集分佈、貼近地面。這種植物的根扎得深且牢,既頂得住颶風,也能在霜凍、乾旱及一切極端難測的高地天候中保住一線生機。就這樣,高山花朵的特色應被視為山的一部分,它的生活方式就是山的存在方式,一切就像水到渠成那樣自然。
提及大山的存在方式,還得講一講那些豔麗的花。雖然不知道它們在山間開了多久,但根據緊貼在一起的花簇大小來看,有些肯定已經挨過好幾個冬天了。大部分山花都是生命力頑強的選手,可即便是趕在一個季節跑完生命週期,選手們也從來沒法確保成果、留下後代。死亡不僅尾隨著個體,還籠罩著整個物種。就算是那些命大的植物,也必須得常常自我更新。只有在某些夏天,昆蟲才能飛上山頂,為了吸引飛蟲,蠅子草的花瓣綻放出熾熱的色彩。
山中稍低處,在所有的山坡、山肩和山脊以及下方的沼澤裡,最具標誌性的植物是石楠,這也正是凱恩戈姆山脈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於石楠在花崗岩中生長得最為繁盛,它的生命也就因此融入了山。山裡長著三種石楠兩種為歐石楠,一種為帚石楠其中最樸素的樅枝歐石楠開在七月一簇簇火紅的花朵就像太陽爆裂的場景,在周圍依然是一片棕褐色的時刻就已怒放。灰白而精緻的輪葉歐石楠在潮濕的地方聚成小塊,通常只有單頭,幾乎像打了蠟一樣,散發出蜜一般的香氣。不過,真正為山丘披上紫色外衣的還是帚石楠,八月開花,看上去雅致宜人,柔軟的光暈可以蔓延好幾英里。假如在熾熱的陽光下漫步其中,最好別選那些已經成形的道路,花香升騰為霧,會教人陶醉不已(我有一個年輕朋友,在她父親讓她跟著時說過這麼一句:「我最喜歡沒人走過的路。﹂)。就像在大熱天行走會被一圈蒼蠅包圍那樣,穿越這片花海時,周身都是石楠花的芬芳。這是因為劃過花海的雙腳會揚起花粉,拂起一陣花香繚繞的煙塵。介於淡黃與淺褐之間的花粉落在靴子上,假如光著腳,就落在雙腳和小腿上;它們有著柔滑觸感,卻也會在手指間留下清晰可辨的細粉。然而,在這樣的花海蹚過好幾英里之後,身體就會變得麻木。和教堂裡過量的熏香教人麻木一樣,花粉過量也會削弱行人對它的好感;只有在智律清明、情感湧動的時候,這種喜愛才能達到最佳狀態。
對於深愛著山中每個季節的人來說,開花之日未必是石楠最好的時光;它長在那裡,在雙腳之下,這本身就已非常美好。在漫長清心寡欲的日子後,腳踏過叢生的石楠,是我所知最可貴的樂趣之一。
氣味—芬芳及香氣—是重要的生命議題,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生命過程的一項副產品。它當然也可能是火的副產品,不過話說回來,火是依靠吞噬活著或曾經活過的生物而存在。氣味也可能源自化學作用,不過即便山上已經死去的生物裡真有隱密的化學反應,我的鼻子也沒能嗅出幾分。我真正捕捉到的氣味,來自生命,來自植被和動物。即便是世上最好聞的氣味之一—土地的芳香—也是一種活著的香氣,因為它產生於土壤中的細菌活動。
因此,植物在生長的過程中散發出各種氣味。有些和花朵的蜜香一般,對昆蟲平添一絲誘惑;有些和石楠一樣,在熾熱的陽光下肆無忌憚地煥發芳澤,也是因為那是昆蟲最活躍的時刻。但在其他情況下,比如冷杉,其氣味來自樹液,來自生命本身。當松樹的幽香一路沁入肺部深處,我很清楚那是生命在源源湧入,穿過鼻腔內的纖毛,進入我的身體。松木與石楠類似,在太陽下芳香馥郁,在林務員前來伐木時,香味也很突出。
生長在山脈低處的所有植被在被砍伐時,要數雲杉釋放的氣味最為濃烈。炙熱的陽光下,它幾乎像是酵素,或是煮沸的草莓醬,不過比後者多了一份讓鼻子和咽喉內膜更緊張的強烈香味。
香楊梅是葉子攜帶香氣的植物代表。這種灰綠色的灌木佈滿山谷澤地,生長在羊鬍子草、茅膏菜、沼蘭、斑蘭和地衣中微小的緋紅杯菌之間。香楊梅的氣味清涼乾爽,和野生百里香一樣,在被擠壓的時候香味最盛。
另一種灌木—杜松—小心翼翼地隱藏著氣味。這種植物有一種奇怪的習性,會成片成片地死亡。咔嚓一聲折斷死去的杜松,就會聞到一股辛辣的味道。有幾個月我一直帶著一塊杜松木,時不時折它一下,就可以聞到新的香氣。這種死木有著灰色的絲質外皮,能夠防雨滲入。即便是最潮濕的季節,森林裡的每
一株冷杉都被淋透的時候,杜松依舊乾燥如初,散發出清晰可辨的熱量。再沒什麼比在杜松折斷時恰好站在杜松林裡更美妙了—能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往攏好的火堆裡添一把落葉松的小嫩枝。有一次,在走進一片低矮的杜松叢前,我用手拂去鬆散覆在它們身上的厚雪,接著一陣令人驚喜的香氣隨之而起,飄浮在凜冽的空氣裡。
生長在低處山坡的樺樹恰恰相反,要靠雨水來釋放氣味。這種香醇的味道就像高年分白蘭地一樣濃郁,在潮濕而溫暖的日子裡教人醺醺然沉醉。它刺激著感官,迷惑著人的大腦;說不清為什麼,整個人就這麼興奮起來。
樺樹枝繁葉茂之時,最不好看。當新葉點綴出綠色的火焰,反倒顯得精緻;等到葉片日漸稀疏,整棵樹便像紋上了金邊。四季之間,最可愛的當屬樺樹赤裸現身之時。太陽低垂,樺樹細枝上絹絲般的絨毛好似光的造物,未經改造,樺樹看上去是紫色的。樹液上行,紫色開始發出耀眼的光,光芒如此強烈,以至於一眼望向山坡上的樺樹群,有一瞬會以為那是盛開的石楠花。
在一片閃爍著紫色光芒的樺樹林裡,間或出現的花楸(rowan)看上去死氣沉沉。裸露的樹枝顯出光滑的灰白色澤,在冬日裡的太陽劃過時一片慘白。十月才是花楸的好時節,到那時,就連一團團漿果的暖色也比不上花揪葉片裡血紅色的光華。這種「被賜福的活木﹂,被認為擁有抵抗惡靈的力量。花楸生長在樺樹和冷杉之間,通常是孤零零模樣;有時又顯得比身邊的樺樹和冷杉高大,在山谷間的小溪旁傲然挺立。
最多彩的月份是十月,遠比六月絢爛,較之八月也更熾烈。生長在低矮山坡的樺樹和歐洲蕨呈現一片金黃,色彩沿石楠根部匍匐生長著的各種不顯眼的植物一路向上蔓延,為苔蘚裹上或蔥郁或橡棕或猩紅的色澤,也點亮了藍莓、蔓越莓、岩高蘭等各種漿果植物。覆盆子的葉子深紅似火,是整個羅斯墨丘斯森林裡最可愛的一員。由於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森林裡的冷杉都被砍倒,每個樹樁周邊都生出覆盆子筆直的細枝。因此,一到十月,一簇又一簇尖尖的火焰便會點燃整片荒原。
一九二○年初夏,一場真正的大火吞噬了這片森林。一位獵場看守員告訴我,為了阻止火勢蔓延,他們四十個人忙了整整十天十夜。據他說,每到晚上,樹幹就像火柱一樣閃閃發光。
如今,原本遼闊的松樹林已經所剩無幾。不過,在大山深處的峽谷中仍然能發現一些古老的冷杉,大概能追溯到原始的喀里多尼亞(Caledonian)森林。埃尼亞赫峽谷裡依然生長著古木,在山另一邊的巴羅赫布伊(Ballochbuie)森林也是如此。艾雷恩湖(Loch an Eilein)的岸邊散佈著極其珍貴的蘇格蘭冷杉,樹周是我臂展(相當長)的二點五倍;剝落的樹皮長達一點五英尺,厚如書本;在地表土壤被沖刷過的地方,裸露的樹根像蛇群一般扭曲交纏。尤其是在埃尼亞赫湖出口處的水閘,不時還可以看到若干樹根,這些早已死亡的樹木中有一半已沉入沼。
這兒和其他湖泊上的水閘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晚期,那時候伐木工的行動響徹整個森林。樹幹整備好之後,只需打開閘門,樹木便會順著匯入斯佩河的水流一路向下。對此,曾有一段來自孩童的生動描述,被羅斯墨丘斯的伊莉莎白.格蘭特(Elizabeth Grant)記載在《一個高地女性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Highland Lady)裡。自從意識到木材是財富源泉之後,人類開始伐木,並在每條溪流旁邊建造小鋸木廠,只需一小塊空地、一把鋸子、一個廚房、一間內室和
一些玉米片即可。不久以後,人們意識到把所有木材順流運往斯佩河更有賺頭,木材在那兒會被用來製造粗糙的木筏,再被運往福哈伯斯(Fochabers)和加茅斯(Garmouth)。這些老鋸木廠的舊址早已被人忘記,取而代之的是卡車、新鋸木廠及其機械設備,用以滿足小鎮的需求。那些並非土生土長的外來者,也會來砍伐、截鋸、切割樹木。不過,那些古老的方式還是留存了下來:某個扎根於此的人,吆喝著一匹本地的馬,把捆在一起的樹幹從人跡罕至的角落拖出來,夜間再趕回荒原邊緣某個古舊的農場。
第一次大規模伐木發生在拿破崙戰爭期間,本土出產的木材成為急需品。一個世紀以後,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在一九一四年以及需求更為迫切的一九四○年,新長出來的樹木步上了前輩的命運。樹最終會再長出來,但短期之間土地免不了傷痕累累,所有活著的生命都會選擇逃離,比如冠山雀和害羞的麆鹿。特別讓我擔憂的是那些珍貴的冠山雀,正是牠們的存在讓這片森林變得獨特。
我曾聽人們說過,尋找這些精緻的山雀常常徒勞無功;不過,假如你知道牠們的藏身之處(我可不會透露具體資訊),只需靜靜站在樹邊,就能輕易地召喚出這些小傢伙。你會聽到一陣騷動和山雀弄出的輕微聲響,但一靠近,牠們就又跑得無影蹤。這時候,只需要繼續安靜地站著,不出一兩分鐘牠們就會忘了你還在那兒,先後輕盈地掠過一根根樹枝,靠近你的頭頂。我看過一隻冠山雀,在距離我眼睛一英尺之外的地方轉了個身。到了築巢的季節,一切可就不太一樣了,這些山雀會變得和罵街潑婦一樣聒噪。我就曾經被一對山雀猛烈地吼過,那勁頭簡直讓人為牠們感到害臊,於是我趕緊離開了牠們的領地。
假如打開湖上的老水閘,水流會多凶猛呢?一位八十歲婦女告訴我,水閘可是能用來對付稅務官的。在班尼湖遠側的凱恩艾爾瑞克(Carn Elrig)下面有一片樹木茂盛的區域,我在那兒迷過路,還有人曾在那裡私釀威士忌。等稅務官上路的消息傳到他耳朵裡時,他已經來不及把酒藏起來了。事實上,比起自己的蒸餾室,他當時離水閘更近,於是他前往水閘。我幾乎能看到他大步向前,腳踏實地,一副蘇格蘭高地人特有的樣子。所以,等稅務官到了,湍急的水流橫亙在他和威士忌私販之間,至少當天他無法過河,可能再過一天也不行。
依據山兩側高處的松樹遺跡判斷,以前這裡的森林要比海拔更高。不過,時不時也能發現海拔位置遠高於森林主體的一棵獨樹,種子大概是被風或是鳥帶過來的吧。在這些離群者中間,有些樹的適應力令人驚歎。它們就像巫師,能夠隨意變換形態。我就知道有一棵植物,長在離兩千九百英尺高的山頂不遠處,生命力非常頑強,枝葉向四周張開,雖然寬不過三英尺,高最多五英寸,卻幾乎稱得上活力煥發。它緊緊依附在那裡,牢牢抓住了荒涼的地表。我很有興趣看看它究竟能長多大,接下來又會朝哪個方向伸展。
冷杉死亡很久以後,樹根會隨樹木的靈魂一起留存下來,成為世上最好的引火柴。有些山裡的老婦人特別看不起用紙引火,也瞧不起花掉一根以上火柴來生火的行為。我認識兩個這樣的老婦,都已經八十好幾,獨居,一個住在靠近斯佩河山脈,另一個在迪河那邊。兩人在荒野裡挖樅樹根,再把它們拖回家砍碎。假如你去拜訪她們樸素的住處,就會看到火滅之後她們用佈滿深紋的棕色手指,把羅塞塔根莖(這是我們在亞伯丁郡的叫法)搭成金字塔形狀,從提桶裡舀出一勺井水倒進水壺,再把水壺掛在搖搖晃晃的繩子上,任它在熾熱燃燒的樹枝上擺動。還沒等你完全適應閒聊的氛圍,茶就已經泡好了。要是陶茶壺的壺口裂了(「我的茶壺掉了顆牙」),茶水會濺到敞開的壁爐上,揚起一陣灰塵和水汽;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說這是在灑茶祭神,不過茶還是那麼香,談話也不會因此失去活力。
石楠叢中隱藏著許多不顯眼的東西,我尤其喜歡石松,不是緊緊纏繞在一起的那種,而是被我們稱為「蟾蜍尾」、毛茸茸的那種。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親就教我採摘的藝術。我們躺在石楠叢裡,我的手指學著慢慢感受每條分岔的小徑、分支,仔細撥開沿途微小的根莖,直到收集到好幾碼長的粗粗一串。這是一門非常適合教給孩子的生活藝術。雖然當時的我還沒意識到這一點,但我確實已經透過自己的手指在慢慢摸索有關成長的奧祕。
山從未完全洩露這個奧祕,人類正慢慢學習如何解讀它。通過觀看和沉思,我們耐心地搜集一個又一個事實。在蠅子草令人生畏的根莖裡,我們發現了一絲痕跡;小米草為了更好地汲取養分,把細嫩的根莖深深扎入草地,顯出一些端倪。祕密,也隱藏在景天和虎耳草的灰綠肉葉裡,那裡存儲著大地饋贈的養分,以備供給不足之需。當羊鬍子草的絲狀細毛在沼澤四周飛舞時,最小的柳樹也蜷起身子,任其毛茸茸的柳絮在高地上飛揚。此外,迷你的杜鵑花努力向外鋪展在山坡上以求保護,玫瑰色的光暈誘惑著罕見的昆蟲在此停留,使它得以和石楠花一樣,在花崗岩上繁茂生長。與此同時,花崗岩卻無法滿足許多其他稀有山花的需求,它們期盼的是石灰岩的紋理,和雲母片岩裡豐富的腐殖質。
比如,最稀有的一種花—高山紫雲英,就只有在凱恩戈姆山脈特定地方才能找到;它柔和的淺色花朵鑲著淡紫色的邊,黑紅相間的常客蝶形錦斑蛾如影隨形。沒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但假如沒有紫雲英,就不會看到蝶形錦斑蛾。有一天天氣潮濕陰鬱,還颳著風,幾乎不太可能看到飛蛾的蹤跡;然而,我們竟然還是在紫雲英花叢裡發現了許多這樣的小東西。
人對土壤、海拔、天氣和有生命的植物、昆蟲之間那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所知愈多(這錯綜複雜的互動裡存在著令人震驚的瞬間,比如茅膏菜和捕蟲堇吞噬小蟲的時刻),這一切就愈神祕。知識不會驅散生命的奧祕。科學家告訴我,活躍在蘇格蘭山地的高山植物群起源於北極圈,這些看上去弱小而分散的植物是我們國家唯一比冰河期還要古老的植物。然而這並不足以解釋這些植物,不過是為難解的算式增加了時間這個新程式罷了。我發現自己對科學家朋友有一種天真的信任:他們是一群如此快活的人,沒必要無故對我撒謊,何況他們講的故事還能讓世界變得這麼有趣。但即便如此,他們這番話還是讓我難以置信。
我能想像岩石的古老,但要我想像一朵花的高齡可就難多了!它意味著這些居於山頂的堅強鬥士,這些有著天使般花序、極具魔力的根莖的植物,狡猾地騙過上一次那長段的冰河期,而不僅是一個冬天。對此,科學家們謙虛地表示,他們也不知道這些生命是如何做到的。
書籍相關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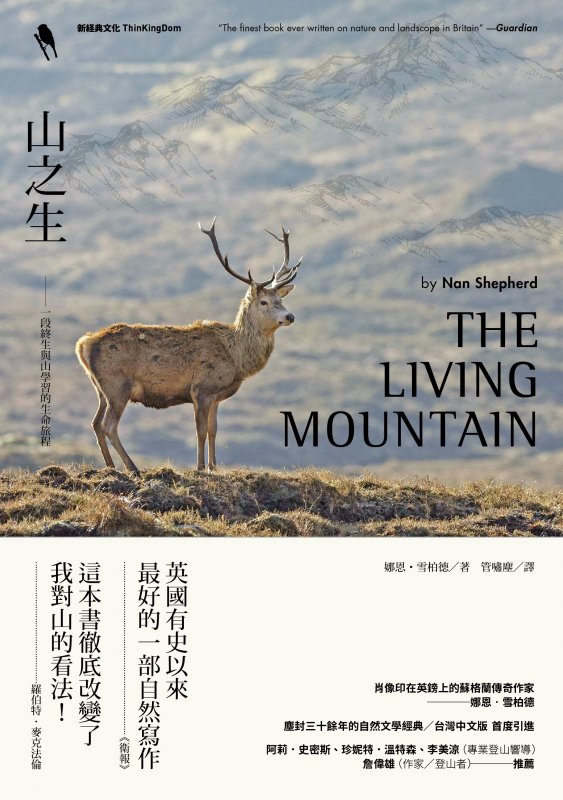
書名:山之生
作者:娜恩‧雪柏德
譯者: 管嘯塵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03月 27